
袁一丹(章静绘)
鲁迅曾在《热风·题记》中追忆“五四”后的情形:“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的新作《另起的新文化运动》起于鲁迅的这段话。
“新文化运动”如何是另起的?为什么要发掘它的“隐藏文件”:刘半农鸳蝴时代的写作、胡适《尝试集》的附录《去国集》、康白情的交际诗和他后来成为“康洪章”的人生、吴稚晖不伦不类的游戏笔墨、留美心理学家的汉字读法研究?《上海书评》专访了袁一丹。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袁一丹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0月出版,316页,69.00元
对于新文化运动,您的新著试图“并置不同的起点,对勘历史叙事的不同版本”,考察其“复数的”开端。具体做法即打捞“结构的‘剩余物’”,包括“被删改的历史记忆、被压抑的精神气质、被排挤的边缘人物、不被承认的文体”,以呈现“新文化系统的两面性”。揆诸既有的叙事和研究,您认为您的工作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改写新文化运动的整体图景”?
袁一丹:我在修改书稿时,不免有一种隐隐的焦虑,觉得自己未能实现“改写新文化运动的整体图景”的抱负。这种改写“总体史”的焦虑,逼迫我去思考自己为什么这样提问,为什么选择这些个案。“剩余物”的概念,是被结构的焦虑催逼出来的,我试图用它来统合书中处理的大部分个案。
这本书的战线拉得很长,回头来看,较之严整的结构,我似乎更关心结构的剩余物,那些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游离成分;较之历史叙述的连续性、同一性,我更感兴趣的是弥散的历史因子及同一性背后的个体差异;较之历史光滑的表象,我更关注结构的裂隙与褶皱。
这本书所做的种种尝试,意在寻找新文化运动中的“隐藏文件”。这些隐藏文件显示出新文化系统的两面性,既有开放的一面,也有封闭的一面。修复隐藏文件的目的,不是将剩余物回填到结构当中,而是用剩余物向结构提问。所叩问的结构,同时指向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过程本身及其层累的历史叙述。
但剩余物很容易被结构“回收”。正如巴特菲尔德指出,即便个案研究已经修正了故事的细节,我们根据这些成果对整体图景的价值重估和对历史轮廓的重新编纂仍然进展缓慢。剩余物中包含的细节,特别是“例外的细节”,在通史或概论性的写作中又被轻轻抖落了,我们仍然按照原有的方式去勾勒宏大的历史构图。
“剩余物”的提法只出现在后记中,不妨看作结构缺失的症候。由此可以引申来谈谈对于年轻一代五四研究者而言,历史综合如何可能。当我们反思历史综合如何可能时,或许已经多多少少感受到历史综合之不可能。正如我们大谈如何激活“五四”,其实已多少意识到“五四”的衰灭。“五四”是近代史的一块超级电池,它的电量是否耗尽,要看研究者能否为它继续充电,使其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保持影响力。
1943年傅斯年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他作为五四运动的当事人,一直不太愿意谈论“五四”。但现在局面不同了,报纸上时常有指责“五四”的声音,而社会上似有一种心愿,即如何忘了“五四”。但傅斯年认为“五四”终归为中国文化的积累留下一个永久的“崖层”,这个“崖层”是不可能湮没的。我将这本小书结集出版,其实是为了对抗某种社会心理,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如何忘了‘五四’”,或者说当“五四”好像没有发生过。从当下的社会舆论中,不难感受到这种“沉默的螺旋”。
前不久给一位朋友寄书,他说更期待一部超越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能在通史的架构中把各种细节和人物的复杂性适当呈现。这种规模的专题史,很大程度上要综合其他人的研究,不可能完全自己打地基、起高楼。2019年我给《东方历史评论》推荐五四研究书单时,也表达过类似的期待与遗憾。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这应该是让新一代五四研究者坐立不安的事儿。在精耕细作的专题论著之外,我们仍缺乏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通盘认识,这种全景式的认识是一般近代史教科书或教条化的通史写作难以取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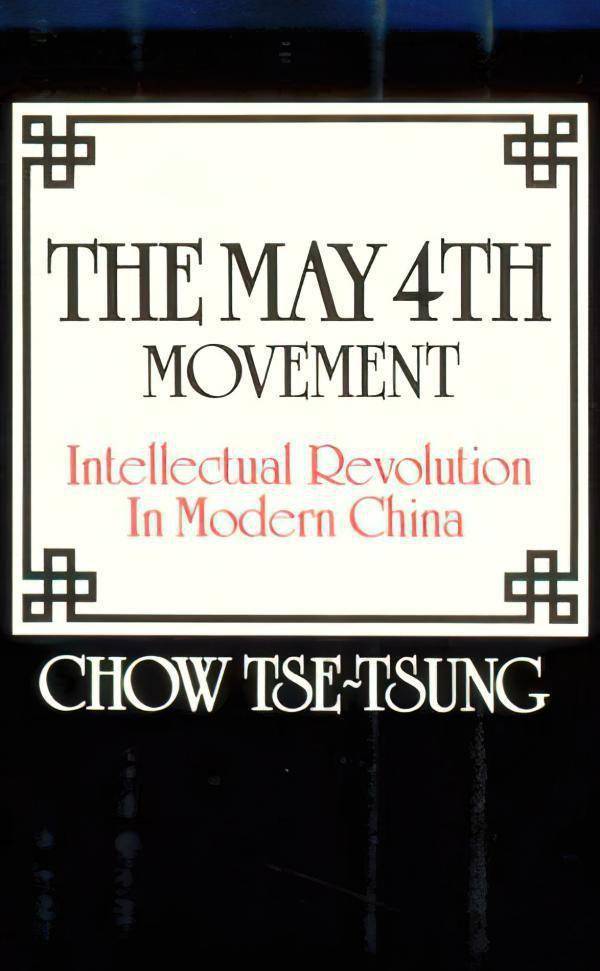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1960)
所谓“改写新文化运动的整体图景”,可理解为重写“总体史”的冲动和抱负。“总体史”旨在给一个时代画像,重建一个文明的整体形式,在一个时期的种种现象之间寻找凝聚性的法则。而福柯则提出另一种历史结构的呈现方式,他称之为“一般史”。“一般史”展现的是弥散的空间,关注历史的非连续性,包括:过程的极限、曲线的拐点、运动的反转、振荡的界限、运行的阈限、因果关系的错乱瞬间等。我这本小书的面貌,或许更接近关注弥散性、非连续性的“一般史”。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标题来自鲁迅《热风》题记。您梳理了北大派(《新青年》《新潮》)、在“五四”后发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研究系(《时事新报》)和将“新文化运动”反套在北大派的学衡派(《学衡》)三者的关系,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或为态度之别,或为新派内部的正统之争。您能谈谈对周作人所谓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乃通过五四“焊接”在一起的说法的理解吗?您怎么看年初大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以北大为主的叙事?
袁一丹:我进入五四新文化研究的起点,就是鲁迅《热风·题记》中的一段话。我抓住里面的两个关键词:“另起”和“反套”,作为扳手来拆解以《新青年》为起点的新文化叙述。“另起”指向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反套”则指向学衡派的张冠李戴。这种解构性的提问方式,暗中制约了我的研究取径和所能抵达的终点。
整本书的方法论意识,用丸山真男的话说,就是将已经知晓的结局还原到不会知道如何发展的未知混沌中,将既定的历史进程拖回到蕴含了多种可能性的历史原点上。以语词、过程、个体为支点,撬动固有的五四新文化论述。
首先是对语词的时态的敏感,把作为历史概念的、过去完成时的新文化运动,还原为打上引号的,现在进行时的“新文化运动”。其次是浑朴的过程的观念,追问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如何“焊接”在一起的。最后是在五四大合唱中留意倾听不合时宜者的声音,注意新文化的排斥机制及自我压抑的面向。
我对正在进行时态的“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主要是从报刊中来的。我曾系统翻阅过北大派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北大日刊》,研究系的《晨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解放与改造》,以及国民党系统的《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当年翻阅原刊获得的历史现场感,是数据库检索无法取代的。你对你所使用的每条材料的上下四旁都有一定的把握。
您提到我书中援引周作人的一个说法,他认为“五四”从头到尾是一个政治运动,前头的文学革命,后头的新文化运动,是“焊接”上去的。我正好借这个说法,谈谈文学研究者和史学研究者处理材料的手法有何差异。近代史研究者也会用到这条材料,但一般只是作为一种观点来引述,不会特别留意周作人是在什么时间点上,在怎样的上下文中说的。文学研究者则会对材料的出处、语境、措辞更为敏感。
周作人的“焊接”说,出自《北平的事情》一文。这篇文章写在1949年1月,周作人出狱前后,采用主客对谈体,主人有北大背景,客人是燕京大学出身。这篇对谈以北平为主题,是因为当时华北战争吃紧,平津被围。主客二人在围城中聊起北平作为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是五四运动造就的。主人问,如今“吃五四饭”的有哪几位?燕大人以旁观者的口吻,谈起他对“五四”与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理解,用了“焊接”一词。

周作人《北平的事情》
“吃五四饭”这个词在周作人这里,暗含讥讽,或指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在收入《知堂乙酉文编》的《红楼内外》这组回忆文章中,周氏谈到黄节、孟森之死,说“北伐成功以来,所谓吃五四饭的飞黄腾达起来,都做了新官僚”。有趣的是,胡适藏书中有一册《知堂乙酉文编》,胡适用红笔勾出这句话,把“吃五四饭”的“五四”二字叉去,改为“革命”。
“焊接”说并非出自主人之口,而是借“吃不着五四饭”的燕大人之口道出。留意这条材料的史家,自会从中提取出一个观念,即周作人强调“五四”的政治性,在他看来“五四”与《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和之后勃兴的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回事。但我觉得更有意味的是,周作人为何要在平津围城时,以获罪之身重提“五四”?又为何用主客对谈体包装自己的观点。如果隐去1949这个时间点,忽略了围城的空气,忽略了这篇集外文的特殊文体,就容易把“焊接”说当作周作人一贯的立场。
今年热播的《觉醒年代》唤起了普通观众对这段历史的浓厚兴趣。据我观察,这部剧的观感相当两极化:普通观众看着过瘾,认为这部剧打破了五四人物的刻板印象,把正反两派都塑造得很鲜活。而这部剧在专业圈内的风评不高,文史研究者纷纷表示看不下去,认为这部剧对人物关系的处理太想当然了,有些场景是编剧脑补出来的,好像给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都加了一层滤镜,使其符合当代人的审美与想象。

《觉醒年代》剧照
您问如果《觉醒年代》不以北大、不以《新青年》同人为剧情主线,又当怎么来拍?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以北大及《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叙述深入人心。自1920年代起,北大作为五四策源地、《新青年》作为新文化的金字招牌,就被运动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共同建构起来,并以五四纪念的名义被反复书写。要在北大这个中心舞台外,呈现复线的历史,需要研究者有敏锐的嗅觉,才能发现那些被删除的“隐藏文件”。比如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彭鹏、高波、周月峰等学者已有很扎实精到的研究。
台湾地区学者陈以爱的新著《动员的力量》提示我们注意以张謇为首的“东南集团”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东南集团”的核心人物如黄炎培、沈恩孚、聂云台、穆藕初等,在以往的五四研究中关注不够。我当初在翻阅原始文献时也曾注意到这些人的身影,但受限于以北京为中心的思想史视野,没有将这些穿梭于学、商之间的幕后人物纳入考察范围。“五四”前后东南士绅的运作谋略,既与北大派暗中呼应,也有自身的人事布局与利益考量。近年来关于研究系、江苏省教育会及五四地方史的研究,正在逐步改写以北大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论述。至于何时这些专题研究能进入大众视野,进而改变其对五四新文化的整体认知,还有待大量的学术普及及影视改编工作。
“五四”后,“运动”一词崛起,新文化在各地被追随模仿,形成了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和权势落差。您认为地方军阀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您能谈谈《新中国》杂志、阎锡山和胡适对于“主义”的态度异同吗?
袁一丹:我们从思想史层面考察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时,常常忽略南北对峙与地方割据,而把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当作统一体。新文化与地方军阀的关系引起我的注意,主要是因为《新中国》杂志。这个杂志在新文化出版物中销路不错,却被罗家伦斥为冒牌货。我在翻阅胡适来往通信时,发现《新中国》杂志与胡适的关系,或是他在背后主持的。《新中国》最招人非议的是它关于山西新政的集中报道,在此我想再补充一点材料。
1919年蒋梦麟主持的《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沈恩孚、庄俞合著的《山西之政治与教育调查录》。《新教育》是江苏省教育会创办的刊物。沈恩孚将山西之政治视为教育的政治,在阎锡山主持下,“不啻以山西一省,为极大之学校;而自为校长,以教导全省人民”。经亨颐在《山西究竟怎样?》中指出,阎锡山以督军兼省长,是山西新政发生的最要条件。阎氏用做校长的办法,来做督军省长,把教育之职揽入自己名下,因此山西的教育不是教育家的教育,而是督军省长的教育。有人批评山西是阎锡山一人之山西,山西的创造精神是“非民治”的创造精神。

阎锡山(1920年)
自1917年阎锡山以督军兼省长之后,推行所谓“六政”:植树木、兴水利、育蚕桑,属于兴利;禁烟赌、剪发辫、放天足,属于除弊。“六政”中成效最显著的是放足。据沈恩孚调查,山西各县设“天足保婚会”,又令小学校学生佩带“不娶缠足女子”徽章,以保障放足者必得婚配。山西强迫放足的政策有矫枉过正之处,连老年人也一定要她放足,路上有小脚的经过,立刻要验看有没有脚带,吓得妇女不敢出门。
阎锡山主导的山西新政,采取军、政、教合一的模式。军署内设有大讲堂,经常请中外名人演讲,阎氏必亲自出席,并要求省城军政要员一律听讲。此外还设“洗心社”、建自省堂,参以宗教仪式,让军政人员定时自省。这种军政教合一的教育模式,在高一涵看来,比没有教育还可怕,在青年脑筋中装进去许多乾隆嘉庆年间的思想。
阎锡山的山西新政,与“五四”前后的新教育、新思潮似有某种同步性,但若细察这些举措的用心、手段及效果,尤其是军、政、教合一的模式,与新文化的核心价值并不合拍。需要从山西所处的政治军事环境,理解阎锡山的治理术。1926年《国闻周报》上的一篇征文从政治、教育、经济、民生多方面剖析阎锡山统治下之山西,作者吕承言认为在历次政变中,山西总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而窥晋之野心家时潜时浮,阎氏为自卫计,不得不倾力于军事准备,而未能将新政的表面文章落到实处,改善民生,实现“用官不如用民,用民不如民自用”的理念。
加入《新青年》阵营后,刘半侬为洗刷“《礼拜六》气”,“跳出鸳蝴派”,改名刘半农,以求再造自我,融入文学革命的事业。刘氏在上海卖文时期最擅长侦探小说和滑稽小说,怎么理解这种文类选择?这与他后来形成与周作人不同的对通俗小说的理解有关吗?您会如何比较鲁迅和刘半农大半生的自我清洗?
袁一丹:刘半农这一章的写法,带有精神分析的意味。我把从“半侬”到“半农”的更名,看作一种自我的“再生”(second birth)。“初生者”和“重生者”是威廉·詹姆斯探讨“自我分裂与统合”时提出的一对概念。对于“初生者”而言,世界是直线构成的,它的价值系统由同一种单位计算;但对于“再生者”而言,世界是二三重乃至多重的构造,每重世界又各自矛盾,他随时可能陷入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当中。
“初生者”(once-born)往往是心态健全的乐观主义者,世界在他眼里永远是蔷薇色的;“重生者”(twice-born)多具有双重人格,容易感受到虚无主义的来袭。他心头住着两个鬼,这两个鬼没办法和平共处,时常争执、打闹,导致自我的撕裂及无穷尽的内耗。胡适的人生哲学,接近于威廉·詹姆斯所谓的“初生者”;而刘半农、周氏兄弟的精神气质,则更接近“重生者”。
刘半农在上海卖文时期的小说创作,尤其是侦探小说创作,有一个特点,我称之为“非沉浸式”写作。小说家不是单纯的讲故事的人,而是以下层社会的研究者自居。刘半农认为自己涉足侦探小说这一领域,长处在于随处留心“中国中流以下之社会之心理及举动”,“即通人达士之斥为三教九流而不屑与交者,亦无不待之以礼,唯不为其同化而已” (《匕首》前言)。刘半农在小说中刻意插入大量“切语”,即民间隐语、市井行话,如谓傍晚行窃为“灯花把”,清晨行窃为“露水把”,搜身为“洗山头”等。
侦探小说《匕首》中有个细节颇能说明我所谓的“非沉浸式”写作。这篇小说设置的讲故事的场景在一艘夜航船上,船上燃着一支牛油烛,本是营造氛围的道具,作者却借题发挥道:“以物质文明之二十世纪,以四千年古国之中国人,以江苏开化最早之无锡,而犹舍钟表而不用,用此野蛮时代之计时法,中国人好古之特性,岂世界各国所能及?”这段溢出的议论有自高位置之嫌,属于典型的“非沉浸式”写作,刘半农有意将叙事者与他笔下的“下流社会”区隔开来。
周作人把通俗文学当作有待分析的病例,用医生的眼光加以审视;刘半农从鸳鸯蝴蝶派中跳脱出来,当他倒戈一击时,对“为社会所唾弃、被社会所侮辱的”下等小说自然融注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和道德关切。

1921年5月,刘半农(中排左一)与蔡元培、章士钊、张奚若、陈源及徐志摩、傅斯年、张道藩等人在英国合影。
您说您这本书是“文学研究‘历史化’的产物”,同时又是以“回归文本”的方式对这种趋向的“自我纠偏”。请您谈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关系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您认为我们今天可以如何重估新文化的价值内核?
袁一丹:在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过程中,王瑶先生特别强调这一学科的历史品格。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是把现代文学作为一个过程加以把握,注重历史发展脉络,注重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注重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王瑶先生反复强调现代文学研究者要有历史眼光,所谓历史眼光,按钱理群老师的解释,就是要养成两个基本观念:“过程”和“联系”,由此形成一种历史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化”是现代文学研究确立自身学科主体性的内在要求。
如今打通学科壁垒,返回历史现场,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某种共识。但打通文史的目的何在?返回历史现场之后又如何?打通、返回,不能简化为某种扩容性的技术手段,而应保持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自觉,不能丢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看家本领,替人耘田。
事实上,对五四新文化的价值重估,目前仍是一张空头支票,难以兑现。价值重估的悬置与延宕,一方面缘于当下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也跟研究者的主体状态有关。年轻一代研究者在面对“五四”这类重大历史议题时,总有一种无力感,甚至是逃避心理。老实说,文史学界正面与“五四”对垒,敢于扎硬寨、打硬仗的并不多。跟前辈学者相比,七〇后、八〇后研究者的优势在于接受过相对完整的、不敢说系统的学术训练,擅于精耕细作。但九十年代以后去政治化的思想氛围和条块分割的学科架构,在无形中限制了我们的研究视野,阉割了我们的学术抱负。一面抗拒宏大叙事,一面又不得不依附于某种替代性的宏大叙事。只有在触碰“五四”这类议题时,研究者才能深切体会到这种无力感,或者说主体的暧昧性。
“五四”本身是政治危机、思想危机的产物。每一次对“五四”的重新阐述,无异于对危机时刻的再度确认。如果我们从当下的现实处境中感觉不到“五四”所包孕的危机意识,或觉得药不对症的话,仅仅把“五四”当作常规历史题目加以技术化的处理,也就意味着“五四”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势能的衰灭,甚至是终结。
在五四新文化这个老题目上,新材料、新方法、新范式催生的研究新意,在我看来,总是暂时的、局部的;真切的危机意识而非危机修辞,才是更新历史解释的源头活水。或许在刻意的遗忘及四面八方的反对声中,而非仪式化的纪念或学院派的研究中,五四新文化的价值重估才显得愈发迫切。
“五四”确实是一个觉醒年代,不仅是历史意识、政治意识的觉醒年代,更是大写的“人”的觉醒年代。在修改书稿时,我一直在想什么意象能代表我心目中的五四新文化。这种统摄性的意象,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物、文本、事件,而是把人事物席卷在内的历史势能。这本书选取罗克韦尔·肯特(Rockwell Kent)的作品“Starlight”(星光)作封面,以此象征我心中的“五四”----大觉醒,亦即大创造的年代。

罗克韦尔·肯特《星光》(1930)
我偶然发现这幅版画的构图竟与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中《补天》开头描述的场景有暗合之处:女娲----人的创造者----仰躺在海岸上,正准备起身造人,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玫瑰色的光海里,脚下是惊异的波涛,起伏得很有秩序。这是觉醒时分,造物者所面对的历史星空。
《补天》要讲述“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可以把我这本小书看作是对五四新文化的“故事新编”。正如黄子平教授所说:旧的“伟大故事”崩散了,碎片在人们脚下四处漂移;新的“伟大故事”远未成形,素材和伪素材如大风沙扑面而至 (《〈故事新编〉:时间与叙述》)。黄子平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为解决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进行的静夜挣扎。今时今日用个人捡拾的碎片,重新编织五四新文化的“伟大故事”,能否找到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之间的紧张感呢?

